

编撰整理:如一
 |
作为一名美国“60后”,安靖如近年来在国际汉学界声誉鹊起,他以“进步儒学”这一学术招牌得到各国汉学家的肯定并逐步奠定其学术地位。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东方文化研究计划”外国学者访华项目,每年邀请一名外国学者访华考察交流,被选中的都是在国际汉学界具有较重分量的汉学家。2016年11月,当得知自己成为“东方文化研究计划”2017年受邀访华学者时,安靖如分外高兴。
一、安靖如其人
安靖如(Stephen C. Angle),1964年出生,美国纽约州人。1987年获耶鲁大学东亚研究学士学位;1994年获密歇根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自1994年起在美国卫斯里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教书;曾为哲学系主任、东亚学院院长;现任东亚研究弗里曼讲席教授与哲学教授。研究方向有中国哲学、儒学、宋明理学、政治哲学、伦理学与比较哲学。出版有《圣境:宋明理学的当代意义》(Oxford, 2009),中文译本在201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推出;《当代儒家政治哲学:进步儒学发凡》(Polity, 2012),中文译本在2015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推出。曾为富布莱特访问学者。2016年至2017年,安靖如教授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当博古睿研究员(Berggruen Fellow)。
 |
| 2017“东方文化研究计划”期间,安靖如在北京大学为学生们做讲座。 |
二、安靖如访华纪行
冬去春来,转眼就到了2017“东方文化研究计划”学者访华项目的实施时间。2017年3月27日,安靖如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背起行囊,踏上了学术交流与考察之路。这一线路包括江西、浙江、贵州、北京。
(一)在江西、浙江分享“进步儒学”
安靖如人高马大、安静从容,行程中,除既定的讲座与交流外,他总是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阅读或写作。无论在飞机还是高铁上,甚至是在汽车上,往往是甫一坐定,他便会打开书或笔记本电脑。
安靖如不只是一名书本上的中国通。从上世纪80年代在耶鲁大学结缘中国文化以来,他数十次来到这里,跑过大半个中国,深谙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他十分关注中国时事,像“雄安新区”等新闻全都了然。中国热门的手机应用程序如微信、支付宝等,他一概用得倍儿溜,摩拜和小黄车更不在话下。
 |
| 2017“东方文化研究计划”期间,安靖如在浙江余姚名人馆内与王阳明塑像合影。 |
许多美国小男孩都听过“在自家后花园一直挖、一直挖,挖到头了就是中国”这样的美丽谎言,安靖如没有。家里也没人跟中国有什么联系,他小时候生活的纽约州,几乎见不到几个中国人。中国对他来说从来就是一个模糊的存在,直到在耶鲁读本科时,因为听了著名汉学家乔纳森•斯宾塞的课,才一发不可收地爱上了中国传统文化。
安靖如从耶鲁读完本科后,又在密歇根大学拿到了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其间,他在中国南京、台北学过汉语,在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洛杉矶学过日语。安靖如曾任美国卫斯里安大学东亚学院院长、哲学系主任,现在是该校哲学系教授。多年来,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哲学、儒学、宋明理学、政治哲学、伦理学与比较哲学。他的主要著述为《人权与中国思想》、《当代儒家政治哲学》、《圣境:宋明理学的当代意义》,其中,前两部著述目前已出版了中文版。
安靖如这次中国行的学术目标之一,就是要与更多人分享他的“进步儒学”。安靖如用英文写作,所以“进步儒学”这一学术名词是先有的英文,后有的中文。学界对他的中文提法有争议,但安靖如还是坚持用这一提法,他并不认为这是个完美的表达,但在找到更好的版本前,他最愿意用的还是这四个字。
那么,“进步儒学”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安靖如的学术主张有哪些?还是通过他与浙江大学师生的对话来一窥“进步儒学”的真容吧。
 |
| 2017“东方文化研究计划”期间,安靖如在浙江大学做讲座。 |
浙江用三天完美的江南雨款待了安靖如。2017年3月30日晚在浙江大学紫荆港校区的讲座,因为连绵不断的春雨,主办方有些担心听众的上座率。结果,能装30人的教室挤下了40余人,部分同学还是从浙大西溪、玉泉校区专门赶来的。
开讲后的安靖如,虽然还是一样的不疾不徐,但眼睛里的神采,让他看起来跟平常很不一样。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章雪富主持了当晚的讲座,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助理时坚东等与浙大学子们共同聆听了讲座。讲座前,章雪富还和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彭国翔、浙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方志伟一同会见了安靖如。
讲座中,安靖如以西方学者独特的视角审视儒家学说,在整合现代新儒家传统与伦理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探讨了儒家基本价值在当今社会的意义。他谈到,“进步儒学”就是要将伦理的进步植根于创造性的政治实践。他认为,传统儒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需要在中国这个宏大的社会体系中发展,并获得与实际相对应的思想活力。
安靖如从“破”和“立”两个方面阐述了“进步儒学”。要立的当然是他的“进步儒学”,“破”就是批判现在一些保守的自称儒者的个别学者的看法。安靖如对同学们说,真正的儒学本来就是进步的。儒学刚刚诞生的时候不过是古代中国一个地区即鲁国的文化,它通过跟不同的学派对话来丰富自身,进而变成一个全国性的学说。到了汉代以后,它又跟别的不同的传统对话,继而形成了新儒学,亦称宋明理学。它就是这样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到了现代,儒学又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它通过跟西方哲学的对话丰富了自身,现代新儒学的发展也因此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进步从哪儿来?安靖如说,其实就是把它认为好的给吸收进来,把它认为不对的去除掉。这就是孔子所讲的“因格损益”。如果你不能保持开放态势、吸收新鲜血液的话,它就会像河流一样干涸,发展也无从谈起。安靖如还以当前年轻人普遍关心的话题作为例子,谈了儒学怎样才能应对当今社会的种种挑战。
彭国翔在安靖如讲座之后作了点评,他对安靖如“进步儒学”的主张表示赞赏与支持。他还给“进步儒学”提供了一个备选译法,即“日新儒学”,用中国儒家经典《大学》中的“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句来表达英文“progressive”一词的内涵。
在设计本次活动行程时,安靖如非常配合,他特别提出要访问的人文景点只有一项,即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书院。因朱熹和学界名流陆九渊等曾在此讲学或辩论,这里成为理学传播的中心。白鹿洞书院以其悠久的办学历史、深远的文化影响而被誉为“天下书院之首”,在中国教育和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安靖如心仪此地,因为他与这个从未到访过的所在神交已久。
 |
| 2017“东方文化研究计划”期间,安靖如在浙江余姚王阳明故居。 |
2017年3月28日,安靖如经南昌来到九江。得知安靖如来访,白鹿洞书院管委会主任黎华作了悉心安排,他亲自前往书院入口处迎接安靖如一行,并安排专家为安靖如介绍书院内的建筑与陈设,还向安靖如赠送了由他本人主编的最新一期《中国书院论坛》杂志。
从先贤书院到朱子祠,从棂星书院到白鹿书院,安靖如漫步于古老建筑间,默默地与宋代文人们进行着对话。
浙江大学讲座的第二天,安靖如还在主办单位的安排下,前往浙江余姚市参观了王阳明故居。位于余姚城区龙泉山北麓的王阳明故居,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其间虽然经过多次改建、扩建,但主体格局未有大的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余姚市持续投入巨资,按照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对王阳明故居实施整体修缮。得知安靖如来访,王阳明故居纪念馆馆长万丽珏亲自带着馆内的优秀讲解员前往迎接,并介绍了故居的基本情况。在王阳明故居,安靖如不仅了解了王阳明的家族渊源,也更深入地了解了他“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心学发展历程。
参观王阳明故居后,安靖如还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参观了余姚市博物馆和余姚市名人馆。
行万里路,破万卷书。美国人安靖如一路追寻中国先贤的足迹,用心感受他们的精神与学说。更重要的是,他还要用一个西方人的独特视角继续深入研究儒学,让儒学为当下的中国与世界做出更多贡献。
(二)安靖如教授贵州访问记
2017年4月1日至3日,正值一年一度的清明小长假,应邀参加“东方文化研究计划”2017年学者访华项目的美国著名汉学家安靖如,在先后走访了浙江王阳明故居、江西白鹿洞书院及在浙江大学进行交流座谈和学术讲座之后,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助理时坚东、中国文化传媒集团董事长外事助理兼国际部主任张小兰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此行返回北京之前的最后一站——贵阳,举行学术交流和公益讲座活动。
 |
| 2017“东方文化研究计划”期间,安靖如在贵阳孔学堂发表演讲。 |
近两年,坐落在贵阳市南郊的孔学堂声名鹊起。在贵州省委、省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全国多所名校著名学者的学术支持下,这个位于美丽的国家级湿地公园花溪十里河滩、占地1300多亩的由民营企业捐资建设的文化项目,正在成为贵州弘扬传统文化和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与基地。
2017年4月2日,安靖如教授穿过一片灿如朝霞的红叶石楠树丛,走进孔学堂明伦堂明德厅,为孔学堂清明系列公益讲座活动拉开大幕,也成为孔学堂第481场社会公益讲座的演讲者。在利用假日聆听讲座的贵阳高校学生和市民的热烈掌声中,安靖如以《儒学如何回应当代社会的挑战》为题,用熟练的汉语阐述了他对儒学的研究心得。
安靖如说,儒学是活的,是与时俱进和不断发展进步之中的,不要一提到儒学,就认为只是过去传统的东西,儒学既包含过去的传统经典,也包括当代不断发展中的新鲜内容,儒学的姿态是开放的,其发展也越来越全球化。安靖如认为,中国儒学界比较关心对经典的阐释,很少考虑儒学在当下的实际应用,建议中国的儒学研究应该多考虑儒学作为人生观如何更好指导人的行为。
安靖如就儒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人伦”为主题进行了探讨。他以“男女关系”为例,阐释了儒学的现代变迁意义。他认为,如果把儒学限定在一个范围之内,就违背了儒学的传统。儒学认为人应该是自由的,人人皆可成圣,这才是其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意义与价值。安靖如说,如果儒学就是古代的那个东西,他担心自己或许会放弃对它的研究。正因为儒学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为当代社会不断带来新的价值,人们才会更愿意去深入研究它。
安靖如的讲座引发现场听众热烈的讨论,听众争先恐后地提问,安靖如都给予了认真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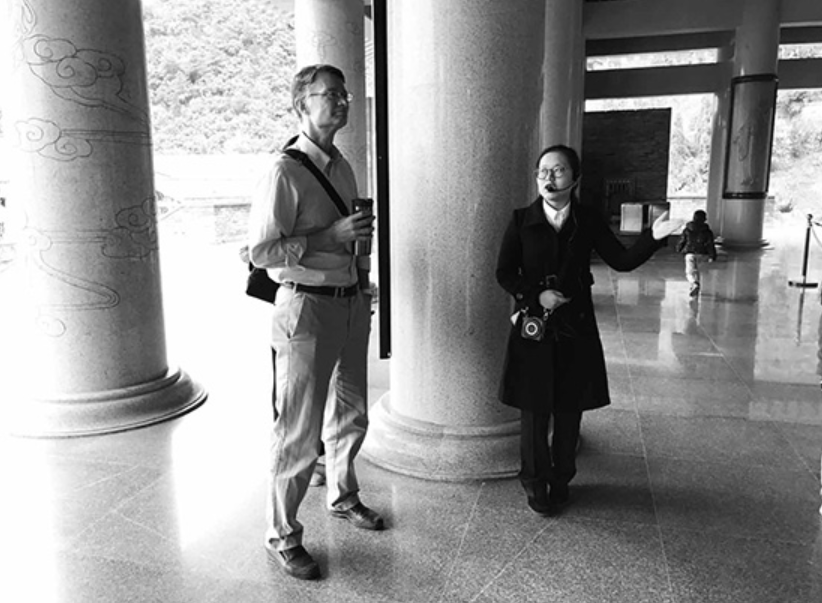 |
| 2017“东方文化研究计划”期间,安靖如在工作人员陪同下参观贵阳孔学堂。 |
讲座之前,安靖如与孔学堂相关负责人肖立斌、龙光斌等进行了座谈,就孔学堂与国外著名高校进行学术合作事宜进行了探讨。据悉,作为贵州文化生态品牌的新名片,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方针的孔学堂,已经初步建成一期的公众教化园区和二期的中华文化国际研修园区,即将开始三期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建设。其中,中华文化国际研修园是集学习、研究、交流为一体的开放性、跨学科、国际化的高端学术平台,旨在为世界各国的学者研修中华文化提供优质便利的平台条件。
孔学堂面向世界发布的研究课题和经费资助项目,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热情参与。望着环境优雅、曲径通幽的教授楼、博士楼和培训楼,安靖如说,期待有一天能够带领他的美国学生,来到孔学堂研修中华文化。
2017年4月2日晚,在修文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周红的引荐下,安靖如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与该院名誉院长、贵州儒学会会长张新民教授座谈,双方就儒学研究和王阳明龙场悟道进行了深入交流。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成立于2002年12月18日,是贵州大学的一个独立学术机构和传播中华文化精神的园地。张新民老师引导安靖如教授沿着2011年5月9日习近平同志到访该书院的路线,一边参观书院的涵远读书楼和培训课堂,一边回忆习近平同志当年在这里与参加读书会活动的贵州大学师生亲切交谈的温馨场面。那次,在陪同习近平同志访问中国文化书院时,张新民深切体会到习主席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和对阳明哲学的重视。
在挂满名家匾额、古香古色的张新民老师的办公室内,安靖如和陪同人员静静地围坐在张新民老师的身旁,一边品茶,一边聆听张新民老师畅谈阳明哲学和儒学感悟。在缕缕的茶香中,张新民毫无保留地分享了他的真知灼见。
安靖如抓住机会,为自己的一些思考寻找答案。他问道,牟宗三提出良知坎陷,希望给法律一点空间,该如何看?张新民老师说,全盘西化派认为中国文化与民主、科学、自由是对立的,民主和科学是最高价值。但他认为,民主和科学只是手段。牟宗三希望良知降下来,给科学和民主让路,是中国刚刚告别帝制的特殊历史时代的提法。中国文化是道德理性做主,发展科学、民主不一定要付出良知的代价,科学技术不能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科学技术转化为战争时,道德是不是还需要到场呢?任何一个环节,良知必须到场,道德必须到场,良知不能坎陷。道德不能够软弱,道德应该很坚强。
一眨眼两三个小时过去了,临行前,安靖如意犹未尽。
 |
| 2017“东方文化研究计划”期间,安靖如拜访贵州大学教授张新民。 |
2017年4月3日,安靖如来到位于贵阳市区西北约30公里处的王阳明纪念馆,参观了阳明洞和玩易窝。位于贵阳市修文县的阳明洞,为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因正义谏言触怒宦官刘瑾而被贬为贵州龙场(今修文县)驿丞时的居留处所,也是阳明先生人生第一所讲学课堂。1938年,爱国将领张学良曾被蒋介石囚禁在此地,度过了大约3年的时光。
明正德元年,遭受四十廷杖而后被关进监狱月余,又经历了一路上的九死一生,最终躲过了刘瑾追杀的王阳明,于正德三年(1508年)春天到达荒无人烟的龙场,最早便居住在修文南门外小孤山脚下的一处“地窝”(一个天然溶洞)里,在洞内研究《易经》,将“地窝”取名为“玩易窝”,并在窝内撰写了著名的《玩易窝记》。在艰苦而安静的环境里,王阳明日夜苦思,忽然有了顿悟,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安靖如感慨地说:“我早就知道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时候非常艰苦,但是亲眼看到这么阴暗潮湿的山洞,看到他当时的真实处境,可以想象当年远比之前想的要艰苦得多,这样的处境丝毫未影响他坚强的内心和成为圣人的修为,令人十分敬佩。”
在王阳明纪念馆内,安靖如在讲解员叶冬梅的导览下,通过图片、文字和模型,观阳明书法,品阳明论道,详细回味了王阳明荡气回肠的精彩人生和儒学道路。这位完美地做到了立德、立言、立功的中国哲学家,在美国哲学家安靖如的眼中,变得鲜活真切了许多,也更加令人肃然起敬。回望纪念馆墙壁上王阳明临终前的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安靖如若有所思。
“收获太大了!”对于此次访华之旅,安靖如由衷地感慨道。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主办、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对外文化传播中心承办的此次著名汉学家安靖如的阳明文化体验之旅,也圆满告一段落。
三、相关成果
(一)与中国文化报记者谈“进步儒学”
一位拥有欧洲多国血统的美国哲学教授,将儒学作为安身立命之学,更立志成为“知行合一”的真正儒者。安靖如,这位来自他乡的谦谦君子,受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邀请,参与“东方文化研究计划”2017年学者访华项目,于3月底到4月初来到中国访学。其间,安靖如做客中国文化报社,与中国文化报社总编辑宋合意会见,并接受了中国文化报记者叶飞的专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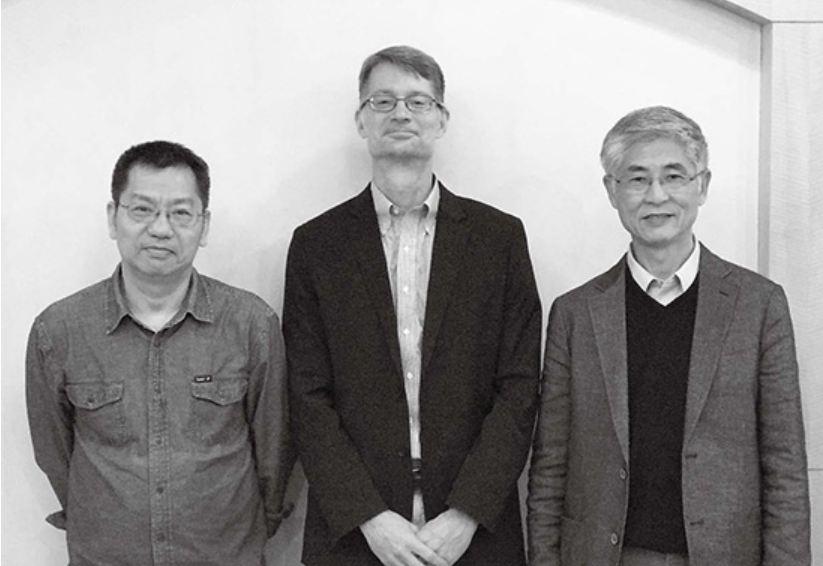 |
| 安靖如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交流。从左至右:干春松、安靖如、倪培民 |
1·儒学要回应当代问题
近年来,儒家学说与现代世界的关系,渐渐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成为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学术与思想领域。数年前,安靖如的著作《当代儒家政治哲学》在中国正式出版,引起广泛关注。现在,其《圣境:宋明理学的当代意义》中文版又将面世。这两部著作奠定了安靖如在汉学领域的地位,推动了中外学界对于儒学的进一步思索、解读和阐释。
“当代儒学,当然不是完全的复古,更不是重复某些僵化的教条。应建设性地发展传统,以当代手段实现传统的核心价值,而不是仅仅模仿传统的形式。儒学要对当代挑战做出回应,针对现实问题做出积极思考。”安靖如开门见山地说,“这看起来很有难度。不过,这并非儒学第一次遭遇时代挑战。”接着,他将宋明理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娓娓道来,指出朱熹、王阳明当年就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曾师承著名学者余英时的安靖如,除了对儒家经典烂熟于心,对牟宗三、杜维明、蒋庆、康晓光等当代儒学学者的学术观点也有着独到、深刻的看法和见解。很长时间以来,儒家学说与自由、民主等非传统价值观之间的互动,成为学术界争论的主线之一。安靖如不赞同过分保守地拘泥于古代传统,也对将儒家直接与这些观念进行嫁接的做法持保留意见。不过,他也认为,儒家学说对中国乃至世界来说,都是独特而宝贵的思想资源,即使学者之间有着激烈的争论,大家的出发点和目标是一致的,即寻求儒学在当代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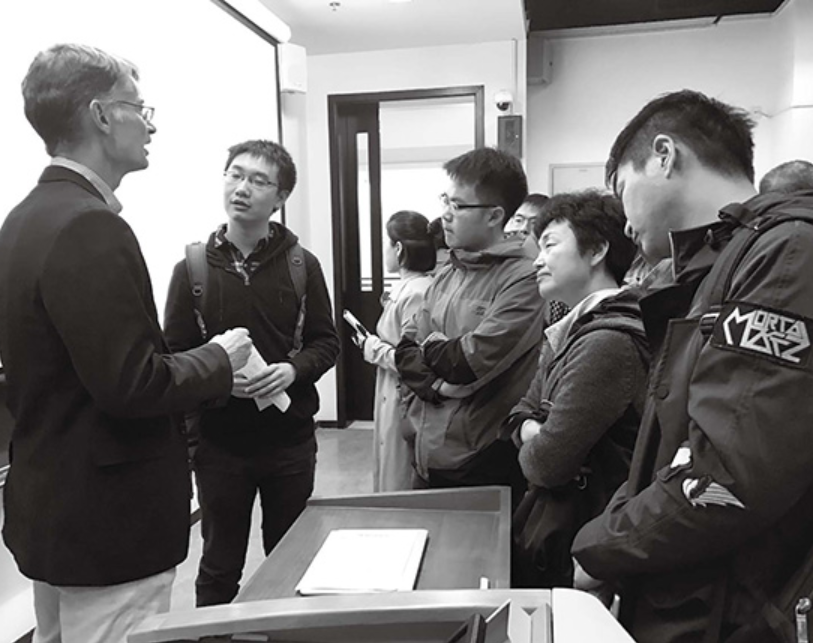 |
| 安靖如在北京大学讲座后与听众交流。 |
2·根植传统的“进步儒学”
儒家学说的哪些内容值得继承,哪些需要扬弃?在安靖如看来,这要从内和外两个向度对儒家的核心价值理念进行评价。所谓内,指的是将儒学视为持续发展的传统,寻求自我批评的可能性。所谓外,即从儒家体系之外的“他者”视角对儒家学说进行评价。
安靖如将自己的儒学观命名为“进步儒学”,强调“活的儒家传统”,认为儒家基本价值的表现形式需要更新、变化,以符合时代的需要。在其语境中,“进步”不是指传统进化论意义上的进步,而指不满足于一种现实形态,去追求理想、超越现实与不断提升。4月7日,安靖如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讲座,并与倪培民教授、干春松教授进行了座谈交流。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哲学系教授干春松认为,虽然“进步儒学”的提法会产生一些歧义,然而这亦体现了作者对儒家与现代世界关系的关注。
“进步儒学”通向儒家政治哲学,基本理论关注“德性—礼—政治”三个维度的相互关系。“这三个维度都根植于传统,在回应新的情景与挑战中有了新发展。”安靖如说,伦理德性是“进步儒学”的最基础目标,但在现实社会,要使这一目标具有达成的可能性,就要遵从礼的规范和政治的、法律的规范。“这就是‘内圣外王’。‘内圣’与‘外王’要同步双修,而不是先‘内圣’后‘外王’。”
在安靖如的阐释下,“进步儒学”不仅要求参与政治,也具有与西方伦理学相比较的基础,并与同样强调公民美德和道德教育的自由主义产生关联,成为与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维度有关联的政治哲学。
3·做一名知行合一的儒者
儒家虽与政治哲学有关,但最关注的还是个人伦理和修养。安靖如与许多学者的不同之处正在于此——他不仅将儒学作为学术研究的课题,更将对儒学发自内心的认同,带入了自己的生活。在安靖如看来,儒者不一定非要“言必称孔孟”,但应“知行合一”,即用儒家学说指导自己的行为,身体力行地提升德性。“圣人”是一种理想境界,一个人如何对待家人、朋友、邻居、同事,如何处理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小问题,其实都是“内圣外王”的具体体现。
安靖如热心公益。在学术研究之余,他常参与慈善活动,现在还兼任当地一个慈善基金会的董事长。他之所以为善,并不是出于其他考虑,而是出于“乐善不倦”的儒家风范,出于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的君子追求。
在此次“东方文化研究计划”的安排下,安靖如一路追随王阳明的足迹,重点走访了浙江余姚王阳明故居、江西白鹿洞书院、贵州贵阳孔学堂和修文县龙场悟道处。实地观摩王阳明生活、讲学的环境后,他对这位大儒、“知行合一”的倡导者愈发欣赏。“龙场悟道处的环境如此艰苦,却丝毫没有影响王阳明修炼成圣的意愿和行动,令人敬佩。”安靖如用“自得”形容这种状态,“这就是儒家,其德性修炼发自不折不扣的自愿。”
值得一提的是,安靖如1994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之后,就开始在美国卫斯里安大学开授宋明理学课程。他的学生在学习宋明理学时,渐渐发现中国哲学对现实生活有着特别的指导意义。有趣的是,由于身边的人对孔子、儒家仅有模糊的概念,在爱人、孩子、朋友和学生眼中,安靖如自然而然就成了儒者形象的代表。
(二)与黄玉顺教授共话世界儒学发展新动向
在2017“东方文化研究计划”结束后不久,安靖如教授与中国儒学家、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黄玉顺于2017年4月25日共聚济南大明湖畔,以“中美儒学对话: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为主题,探讨世界儒学发展新动向。
 |
| 安靖如的妻子和女儿们在南京(摄于2007年,安靖如本人拍摄)。 |
安靖如是西方儒学代表人物之一,创立了“进步儒学”(Progressive Confucianism)理论,他认为儒学传统是活的,在不断发展,他以该理论作为标签以表明其对儒学的看法。“生活儒学”的创立者黄玉顺释义,“生活儒学”意在发掘儒学所蕴涵的某些能够穿越时空、超越历史地域的观念,使儒学能够真正有效地切入当今世界的社会生活。
在阐述中,安靖如指出其理论中的“进步”是指认真描绘出针对个人和集体道德进步的儒家思想核心义务,也代表着自始至终提倡的研究儒家政治哲学路径的特定标签。“‘进步’不是指传统进化论意义上的进步,而是指不满足于一种现实形态,去追求理想、超越现实与不断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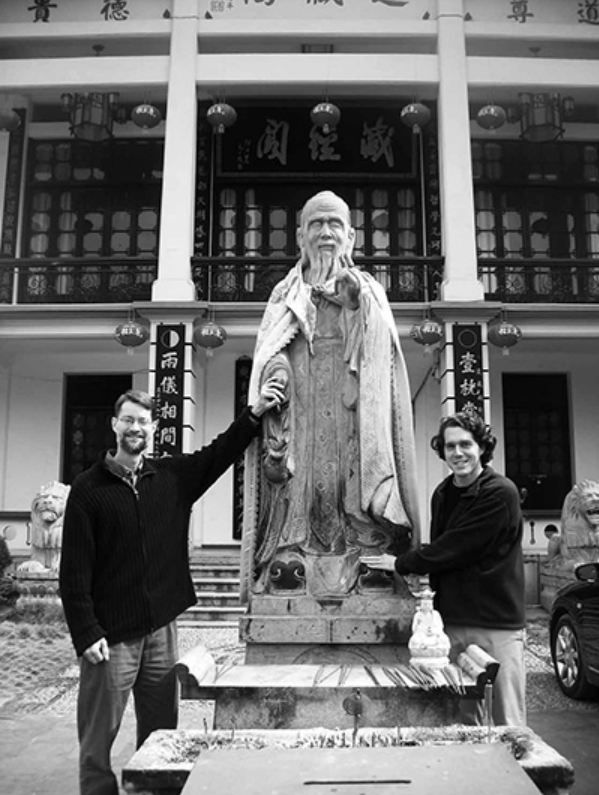 |
| 安靖如在北京任富布赖特访问学者时与方岚生(右,现供职于夏威夷大学)教授合影(摄于2007年)。 |
作为当代中国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黄玉顺,他的生活儒学观点则充分地敞开了重建儒家的可能,使儒学传统摆脱了“魂不附体”的历史尴尬,重新进入当下的生活。
安靖如认为,儒家基本价值在实际生活中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使得当其植根于创造性的实践中时,这些基本价值的实现,能使人生活得更好、社会变得更繁荣。而在创造性实践中实现儒家基本价值的路径,则是使每个人具有与这些价值相关的德行。正因为如此,伦理的广泛社会意义才可能获得与时代进步相同的发展,社会才可能在正常的形态下聚合普遍的力量,从而完成“进步儒学”在全球化时代中的角色担当。
 |
| 安靖如与父亲、弟弟2008年摄于青岛。安靖如的另一个弟弟蒂莫西当年代表美国队参加残奥会帆船比赛。 |
对于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二者的关系,黄玉顺认为两者在思想价值取向上极为一致,但因为生活、文化、学术等背景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判断。安靖如表示,正是因为差异,两者才有合作的基础,共同推动儒学的进步发展,“儒学的研究不能仅仅是学术性的,应该被更广泛的人群接受,这是下一步将继续做的工作。”
(三)与武海霞谈“自由主义儒学”对儒学传统的偏离
在参加2017年“东方文化研究计划”项目后不久,安靖如教授还应邀在中央民族大学做了一次有关“进步儒学”的讲座。中央民族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武海霞在讲座后对他进行了采访。
武海霞:在您最近翻译出版的著作《当代儒家政治哲学:进步儒学发凡》中,您提到“儒家的哲学思维在国际哲学领域中是一个很小但又成长迅速的部分。”您能否介绍一下美国儒学研究的中心议题?美国儒学研究因为直接或者间接师承港台第二代新儒家,可否把美国的儒学研究归入新儒家这个派别?
安靖如:衡量学者学术影响力的一个办法就是看看谁带了最多的研究生与博士生,而这也就意味着对下一代学者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从这个角度讲,3位学者对美国目前的儒学研究具有最大的影响力:倪德卫(David Nivison,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孟旦(Donald Munro,密歇根大学退休教授),安乐哲(Roger Ames,夏威夷大学退休教授)。
目前在美国研究中国哲学的领军人物都是他们三人的弟子。其中孟旦与安乐哲都曾经在香港学习过,并且受到过唐君毅的影响。因此也许可以说港台新儒家对美国的儒学研究有过影响。
但是,事实上新儒家的影响没有那么大。新儒家的一个核心特征——对康德哲学的重视或者用道统来阐释儒学——在美国的儒学研究中基本看不到。这是因为虽然孟旦与安乐哲都曾师从唐君毅,但他们自己的学术背景是多元的,而唐君毅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
此外,他们的学生都是在美国哲学系接受哲学训练,因此他们关注的是在他们的哲学研究环境中的重要问题。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美国儒学研究使用“美德伦理学”而不是新儒家的康德伦理学来阐释儒家的德性伦理观念,特别是倪德卫(DavidNivison)师生流派。但是也有其他研究儒学的人使用美德伦理学。反对使用美德伦理学来阐释儒学的人主要是安乐哲与他的学生们。安乐哲反对使用西化的理论如“美德伦理学”来阐释儒学,所以他和他的合作者罗思文(Henry·Rosemont.Jr.)认为应该使用儒学自有的“儒家角色伦理”来研究儒学。
美国儒学研究中还有一派非常注意研究儒学与心理学的关系。理论研究旨在能实际应用于我们的生活,利用现代心理学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儒学学者(特别是强调德性思想研究的美国哲学家)很快跟上了这一趋势,因为儒学中蕴藏了丰富的对人性的深刻理解。
我想强调的最后一点是:我们前面讨论的问题是哲学系的师生乐于探讨的问题。在过去的十年中,哲学系中从事中国哲学的人数趋于上升,虽然横向比较而言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人还是少数。
除了哲学院系,历史学院与东亚系也都研究中国思想,这两个院系的学者主要研究中国历史与经典文本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像哲学系那样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儒学的哲学观念与理论建构上。
在东亚系,目前主要的研究趋势是试图挖掘清楚儒学早期经典文本的相关问题,以《论语》为例,《论语》在什么时候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文本?在什么情况下才形成这个文本?《论语》中的材料来自哪里?《论语》中是否把不同的观点修正为统一的观点?
美国大部分的学者对中国哲学经典文本的同一性来源保持怀疑(比如《论语》是孔子师徒的问答集、《道德经》为老子所撰等)。
武海霞:范瑞平认为,当新儒家试图将社会民主概念植入到儒家说中去的时候,儒家的思想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现代观念的殖民化。您怎么回应这种看法?您怎么看待儒家哲学“现代化”这一议题?
安靖如: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我的确认为西方的范畴被过多地用于阐释中国思想(在西方如是,在中国也如是),但是另一方面,我也不认为就能够或者应该完全抛弃西方化的范畴。这里涉及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我们必须承认现代化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不是在任何国家都要以相同的方式实现。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各个国家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清晰可辨的相似之处。这就意味着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还是美国人,他们的现代经验有相似性,他们面临的挑战也同样具有相似性。在西方国家,“现代化”与“西化”是一回事,在中国,现代化只是与西方现代化(即“西化”)具有某种相似性。两者的现代化存在差别也存在共同之处。
这就意味着在西方形成的用于解析现代化的挑战与制度的哲学范畴与概念在中国也有适用性。但是,我们也应当了解,因为西方经济权力与文化权力的影响,西方的概念与范畴被过分地使用。
中国崛起就应该包括重新审视哪些概念与范畴是适用的而哪些不是。当然,这一切的前提应当是直面现代化对中国提出的挑战而不是寻求回到前现代中国。我提出过现代哲学家应当使用“有根的全球哲学”的研究方法。
这一方法意味着要在某种独特的哲学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哲学研究(这样的研究就是“有根的”),但同时要充分意识到世界其他重要传统所确认的哲学范畴与价值。其他的哲学传统应当充当新观点的提供者与挑战者这双重角色。只有通过回应它们提出的挑战,文化传统才能得到健康发展。
这就意味着现代儒者在思考儒学发展乃至中国发展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西方的观点。如果在如前所述的方法的基础上使用西方哲学的范畴,则并不必然就意味着文化传统被西方的殖民化。
武海霞:我注意到在您的《当代儒家政治哲学:进步儒学发凡》一书中,您多次提到自己是一个儒者,并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真正的儒者。儒学历史中也有关于正统儒学与非正统儒学的多次讨论。那么,根据您的看法,什么样的儒者才是真正的儒者?什么样的儒学才是正统的儒学?您怎么看待“正统性”这一议题?
安靖如:我先来回答你的怎么定义当今社会真正儒者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一个儒者既需要对儒学过去所取得的成就保持敬意,同时应当尽力维护儒学传统,还要通过回应儒学内部固有的冲突与分歧来发展儒学。
我们尤其需要问自己的问题是:儒学传统所强调的核心价值与目标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在自己的生活中实现这些价值与目标?特别是当一个儒者生活在东亚之外的国家的时候,他所寻求实现这些价值的方法将与18世纪以来的中国儒学大相径庭。当我谈到真正的儒者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时,我是从前述角度看待的。
现在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对于“正统性”这一问题我一直保持谨慎态度。我认为历史上伟大的儒者愿意质疑他们所继承的前代的儒学的权威性。他们寻求从自己新的角度出发来阐释前代儒学。这即是宋明理学所讲的“自得(于心)”,即对道统的一种再创造。
道统本身是重要的,它告诉我们现代儒学传统中最富有启发性的思想。因为儒学传统本身就是多样性的统一,所以道统也不止一个,而道统给予现代的课题也随之不同。尽管如此,强调儒学传统内部的多个发展路径并不意味着现代儒者之间的结论也要大相径庭。
现代化对儒者的挑战是一样的,而儒者回应现代化的挑战的答案也应当基本一致。
武海霞:您是第一位提出“进步儒学”的哲学家,请问您的“进步儒学”提出的初衷是什么?“进步儒学”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安靖如:在我2012年出版的《当代儒家政治哲学:进步儒学发凡》(中文版2015年出版)一书的第一章中,我讨论了几种通行的当代研究儒学的途径。有些学者采用历史研究的路径;有些学者在信仰儒学的同时还致力于其他哲学,如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等;还有学者采用非常保守的立场。我决定用“进步儒学”这一词来表明另外一种思考儒学的立场。
首先,“进步儒学”强调儒学传统中对个人及社会的道德的进步。儒学自古以来就认为人能够并且必须使自己的德性进步,德性进步的终极目标是成为圣人,这当然是极其难以企及的目标。但是,每一个人努力使今天的自己在德性上胜过昨天的自己是可能的,这种在成德上的日积月累,无论是针对个人还是作为整体的社会,是我所提出的“进步儒学”的核心。
进步儒学的另一个核心(也是极大地区别于最近的大陆保守主义儒学的地方)就是当我们站在现代社会的立场反思儒学的核心价值(比如成德)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各种社会与政治的变革是必须的,这些变革是为了给予人们成德的更好机会。有些社会制度压迫特定的社会群体,使他们拥有不够多的机会来成长为更具有德性的人,这种社会制度必须要受到批评,必须要改变。
我在《当代儒家政治哲学:进步儒学发凡》一书中对这一点阐述得更详细,我今年在北京写的论文也主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关注社会与政治变革是“进步儒学”的另外一个维度。
你问的另一个问题是进步儒学与其他现代儒学流派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进步儒学与作为“公民宗教”的儒学的理念不谋而合,或者从更宽广的视域来看,进步儒学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和中国与韩国的儒学研究相契合。
我个人对“自由主义儒学”保持谨慎的立场,事实上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了这一派别的问题。“自由主义儒学”学者中有些人也许同时信仰儒学与自由主义,对他们来说,“儒学自由主义”也许是一个不错的称谓。但是,必须要清楚,进步儒学的基础不是自由主义,进步儒学是一种从儒学自身出发的研究,属于儒学的内部发展,进步儒学从儒学的价值观与概念出发来回应现代社会的挑战。
有一些保守主义的儒家学者采用“自由主义儒学”——或者甚至仅仅是“自由主义”而非儒学——来讨论儒学的发展,但是这意味对儒学传统的偏离,不可能是对儒学的发展与推动。所以我宁愿在自己的研究中完全不去使用“自由主义儒学”这样的概念。
武海霞:您的研究有两点非常不同于大部分美国儒学研究,第一点是您坚持认为自己的儒学研究是有根的儒学研究,即坚持诸如“内圣外王”等儒家核心理念,第二点是您非常积极地与当代中国两岸三地的儒家进行对话,您怎么看待自己的儒学研究的这两个特点,您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
安靖如:我的很多美国同行——就像很多在中国研究儒学的人一样——并不认为儒学作为一种传统在今天依然富有生命力。他们对儒学着迷,是因为他们把儒学当作历史实体来研究,他们想要理解儒学中的思想与理论。
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儒学可以作为指导自己生活的哲学。这就意味着他们追求探索儒学历史中概念之间的联系,但是他们并不一定会研究儒家所追求的理想(比如“内圣外王”)在今天这个时代是否依然有价值;进一步讲,如果这些理想依然有价值,那么这些理想将怎样指导我们现代人的生活。
我很早就对儒学感兴趣,把儒学当作富有现代生命力的传统来研究。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我研究的是新儒家和中国/现代儒学而不是古典儒学:当研究中国现代儒学的时候,很难忽视儒学在现代的改变及其原因这些问题。在我的博士毕业论文中,我花了很长时间来研究梁启超对“公德”的论述及梁启超是如何思考儒学及他所面临的那个新时代。
在我1986年来中国的时候,我发现很容易与中国的学生与老师产生共鸣,因为他们也在思考中国的未来。对他们来说,儒学不是一系列抽象的观念,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可能,可能有助于现代中国发展与中国人民发展这一宏伟工程。
在这样的背景下,很自然地我就想要积极参与到这种中国人关于未来的思考与儒学前途的思考中。我先后去过台湾、香港、南京、北京和中国其他一些地区和城市,我的感觉是中国是多元的,但是同时也面临挑战。
我作为一个哲学家的训练使我了解对话是一种表示尊敬与互相学习的重要手段。对话意味着发问、批评,也意味着愿意接受批评。只有通过这种对话的方式,一种文化传统才能有所发展。